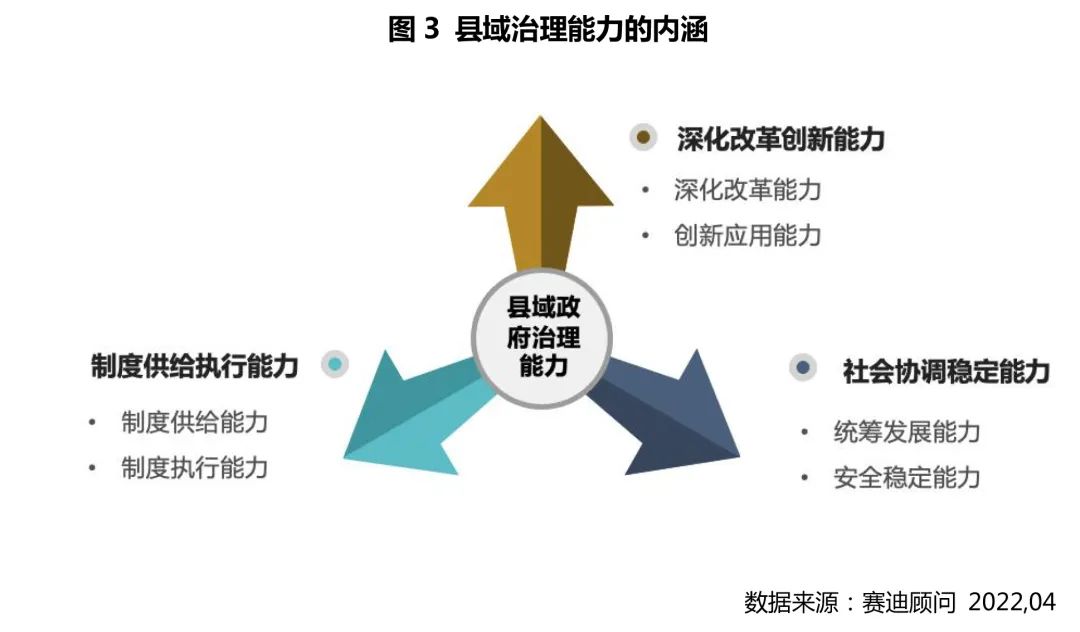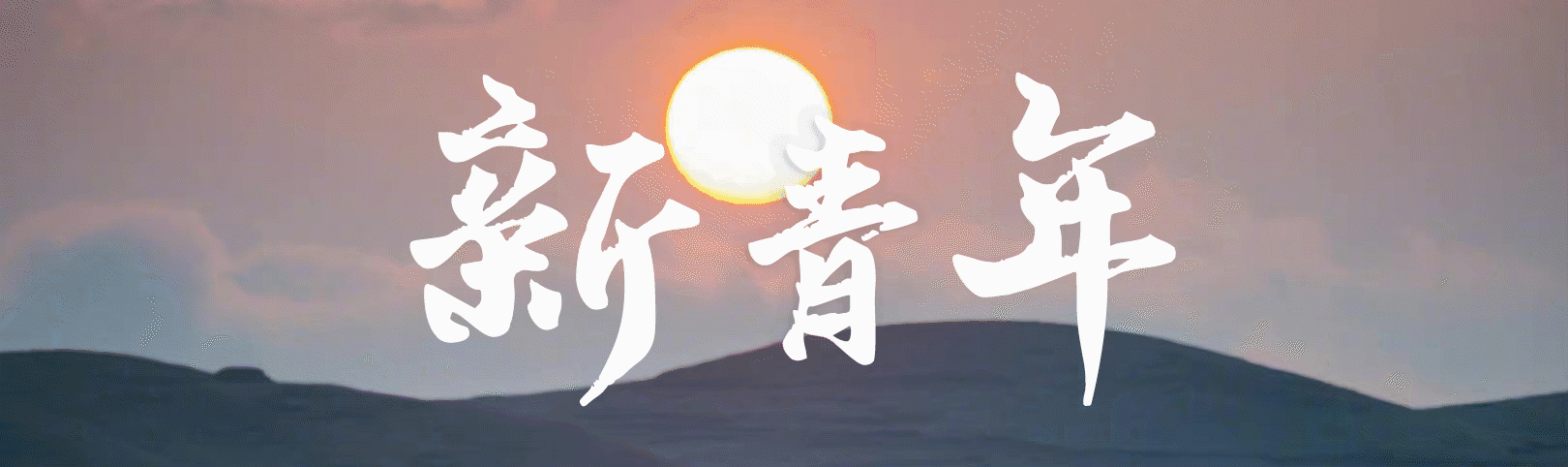
蜘蛛入我床上
昨晚靠在床上,不经意间睡着了。凌晨三点多醒来,却发现手机屏幕还亮着,上面正趴着一只巨大的蜘蛛。
它大概有四个字符那么大,在我惺忪的睡眼里显得突兀而又醒目。它分外惬意,像是舞台中央的歌手一般毫不怯场,又如走红毯的明星,踩着手机屏幕的荧光,享受着在黝黑的夜里熠熠生辉的时刻。
可惜我醒了。急忙吹一口气,把它吹到了黑黢黢的地上。不知道它又会爬到哪儿,可能是床下,也可能是墙角,但这已经无关紧要,一个令我如鲠在喉的问题浮现出来——床上会不会还有蜘蛛?
我打开灯,从枕头开始找起,把被子抖了又抖,确认过没有蜘蛛的活体和压扁的尸体后,才略显僵硬地重新钻回被窝。瞥了眼时间,已经三点半了。
世界依旧静悄悄,但很少失眠的我却睡不着了。
突然觉得嗓子干,仿佛有东西攀附在嗓子眼,不停地咳嗽。脑子则在反复推算着蜘蛛可能的身世,它是谁,从哪儿来,又要往哪儿去?我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,在这个轻寒的夜晚,我却在为一只陌生的蜘蛛深思熟虑。
过了很久,我才睡着,却误入了噩梦的门径。梦中,从枕头下、床缝间和被套里爬出了大量的蜘蛛和壁虎,那蠕动的姿态和扭动的身体,以及擦碰我时的触感,无不让我大脑一片空白。可它现在正在做梦呢。于是,到了某个顶点后,我无奈地醒了。看了眼时间,才五点。
我决定起床。虽然都是醒着,但起床后和在被窝里却是两种不同的状态。后者难以摆脱梦境的影响,甚至有一定几率让梦境续写,而前者会让身体迅速分辨出梦与现实的区别,并让梦的印象黯淡下去,让日常的逻辑与理性发出光亮。
坐在桌前,恍惚间分不清三点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醒来过。喝一口水,过了一会儿,才让身体恢复到健康而舒适的状态。
我开始思考,我本是不怕虫子的,可为什么那时却会寒毛直竖,心底扬起强烈的抵触?
古人曾用“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描述过月份的特征,刘亮程也曾写过《与虫同眠》,人和昆虫本是极好的玩伴。同样,记得儿时,我时常会往房间里放一些蜻蜓之类的昆虫,当时觉得甚是好玩的事情,为何现在反倒有了折磨我的力量?
当我为自己刻画年轮时,是不是被它切断了其他的线条?
我越来越爱干净了,却更像一种精神洁癖。在某种意义上,我在一步步地远离自然。远古的人们,天为盖,地为席,虽不通兽语,却和自然和谐相处。而我和原生态之间,却隔着一道又一道的加工、清洗与消毒的工序。苍茫大地与村庄田野,像是地平线之外的词眼,陌生而黯淡。
想来,自然中从不存在纯粹与洁净,即使是晶莹剔透的水,里面也有无数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物。干净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性的词语,而能够接纳这个世界的不干净、不完美的人,才是真正的干净。因为干净是一种善,一种不建立在损人利己上,而是表现为以己度人的美好品格。也因此,它才能够居于世间万物之中,成为大自然里其乐融融中的一份子,而不是用疏远与排斥超脱其外。
况且蜘蛛也是干净的缔造者,等夏天到来,屋子里嗡嗡地飞着苍蝇,蚊子像无人机般绕着我的头盘旋不停,我又会怀念起蜘蛛的美好。
所以,我为什么就简单粗暴地把它们作为脏的借代了呢?只是因为它们外貌丑陋,灰头土脸,“上不得台面”吗?而美与丑又岂是如此肤浅的定义?看来我也有以貌取人的狭隘。
我不禁感到一阵歉意,虽然平日里向往着万物有灵、众生平等的悲悯与博爱,但当我私下里实践自己的准则时,却依旧落入以自我为中心的窠臼。
我也为自己找到了答案——我从有蜘蛛的地方而来,往没有蜘蛛的地方而去。可它是如今的标准答案或是我想要的答案吗?昨夜的焦灼,便是对它的解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