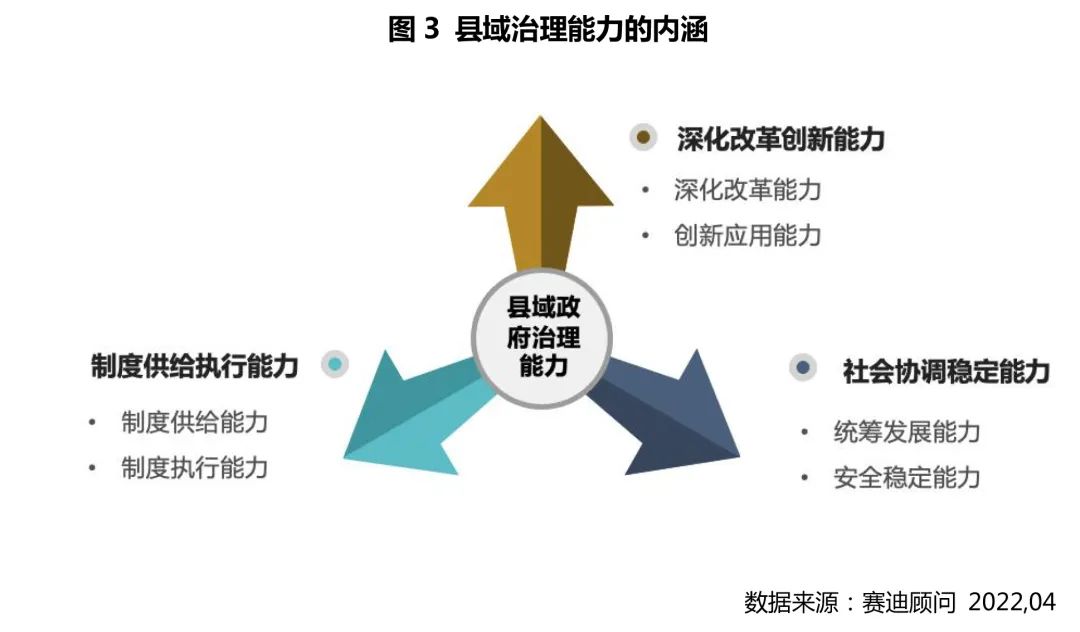上个世纪,洛西的乡间人家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土灶。
那时冬天没有空调、地暖,最好的去处就是蹲灶口。稻草或桑梗做的柴火烧得哔啵作响,灶膛里流淌出红彤彤的暖意。如果烧的是芦苇杆或者废毛竹,那声音简直赶上放鞭炮了,噼噼啪啪的,好不热闹。
猩红的火苗舔舐着黑乎乎的锅底,照得人脸也红彤彤的。家中的烧火凳比寻常的小板凳要长些,祖母和我并排坐着,花狸猫跳到我膝上。烧龙糠(稻谷壳儿)的时候,祖母有节奏地朝灶膛里一把一把扬着龙糠,我则兴高采烈地拉着风箱,煽风点火。
有一次,我拉风箱过猛,火蛇竟从灶膛飞蹿出来,把我的刘海和睫毛都烧焦了,害得我好几天都不敢出门见人。伴着拉风箱发出的悠长而又黏糯的“哧嗒哧嗒”声,蓝红色的火苗轻快地舞蹈,灶膛红得像一座透明的小火山。
听到铁锅里“哧啦哧啦”结饭糍的声音,祖母便停止添柴了。饭烧好了,余烬尚温,花狸猫还盘着粗圆的尾巴懒洋洋地赖在灶膛里,不肯出来。于是,祖母嗔怪:真是只煨灶猫。
农历年底,家里要烧笋干、蹄髈、猪头、猪尾等。这些都是硬货,要用硬柴(树木的茎枝等)烧煮很久。腊月起九之时,父亲开始给房前屋后的树进行修剪,修下来的枝条树杈正好用作过年烧火的柴薪。
我最喜烧硬柴,因为能延烧好久,把几截粗大的树干扔进灶膛,就可袖手旁观了,只当它是一只取暖的火炉便是了。而且,锅里炖肉食,灶口暖烘烘,灶头白软的肉香氤氲,哪里还有什么寒意。
饿了,偷偷起身用锵刀在锅里盛点肉或者笋干丝来吃吃。蹄髈和猪头猪尾是不敢碰的,过年要用。觉得无聊时,还可以从柴房里捡几个番薯来,煨番薯吃。要挑些身材细长匀称的番薯,扔进灶里,用火钳把它们埋在通红的硬柴底下,没一刻钟,就闻得到焦香了。那时,只消做个满嘴烟灰的饕客吧。
跟土灶相关的趣事很多。譬如,刷锅灰。锅灰有个非常诗意的名字——百草霜。我家中每月会刷一两次锅灰。头上裹着蓝白方巾的祖母,手脚麻利地把大铁锅从灶上卸下来,拎到屋外的弄堂里,再将其倒扣过来,左手拿锅,右手执一长柄铁刀,一层层把黑色的锅灰轻削下来,扑簌簌落在泥地上,直削到锅子外面由煤黑变成青灰。 我全神贯注地观看,像欣赏一种艺术表演。
土灶给我的欢乐远不止这些。犹记得,白乎乎的热气蒸腾,母亲边揩着额头的汗珠,边不停地在青晃晃的大铁锅跟前,用铁铲翻炒着糯米的场景,乡间称作“炒糙米”。铁铲碰到米粒和铁锅发出沉闷而有节律的“砰砰砰”声,把糯米炒到由洁白变成褐黄,直到散发出摄人心魄的焦香为止。
糙米粥口感松软,易于消化。我坐月子时,脾胃虚寒,母亲就用土灶上的大铁锅给我炒了些糙米,煮冰糖糙米粥给我吃。用土灶做糯米饭糍也颇有趣味。灶膛里的火需烧得不温不火,这样锅上结的饭糍才不至于焦掉或脱锅。
涂饭糍,不能用力过猛也不能着力太轻,要像粉刷匠那般手腕灵活。用锵刀吸住一个糯米饭团,在大铁锅上一圈圈一层层涂抹,直到又白又香的饭糍厚薄均匀地粘在锅上,再不紧不慢地把饭糍从锅上锵下来。刨花似的,一卷卷,摊在竹匾上冷却。饭糍经滚水一泡,加点绵白糖,瞬间变成梨花朵朵,尝一口,甜香软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