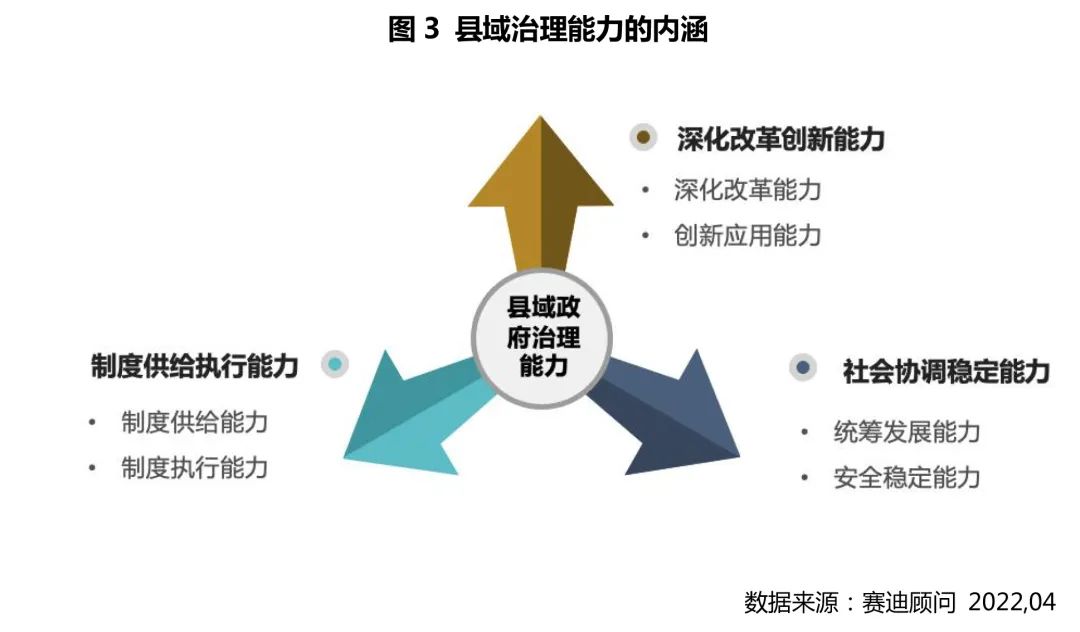天真的冷了。但是,童年的冬天更寒冷。
“呼——呼——”朔风中飘起了雪花。石板路上少有行人。
“热茨菇哎——熟地栗。”午后,街头徘徊着提只夹层棉兜元宝篮,撑把旧纸伞的叫卖者孤独的身影。他那一声声吆喝,在风雪中回响着嘶哑,怆然的颤音。
父亲突然收起摆在老屋街口的杂货小摊头。而后,化二分钱买了五六只热茨菇,合在双手中,折身进了老屋的弄堂,“嗵嗵嗵”,大步流星回到家里。正在做针线活的母亲,立马解下围身布,接过茨菇包裹好。父亲拿了只饭碗,匆匆出了堂屋,去酱园店零拷了五分钱的黄酒后,重回家中。
八仙桌旁,时而围在母亲身旁,听她讲戏文里故事;时而到弄堂里追逐暖身的我和弟弟,捱到了父亲身边。四只小眼睛,直盯盯地看着父亲的一举一动。
父亲从布包里摸出一只茨菇,扳下茨菇柄,连皮带芯,由粗到细,嚼进嘴里。然后,呡了一口黄酒。
这一嚼一呡,动作缓慢,父亲好像很享受茨菇柄,黄酒味。我们的眼睛瞪得更大了。
那只去了柄的茨菇,在父亲手里转了两个身,他选中了蒂部的皮端,用手指甲掐着,慢慢撕下。皮不厚,也光整。不过,它还是带着一点点茨菇的肉。父亲把皮放到嘴边,用牙齿细心地啃了一遍。这个动作,乡间称“脱”,类“舔”,含贬义,指穷酸相。转眼,那茨菇皮经一“脱”,就成了皱巴巴的一坨——它连皮带肉,都成了父亲下酒的一口小菜。
嚼着茨菇肉时,父亲的嘴里发出了“吧叽吧叽”的声响。尽管那只是小小的一口,可他就像在吃大鱼大肉,咀嚼了许久才咽下去。于是,又呡了一口酒,抬起头,深深地呼了一口气。
父亲的眼睛和我们四只小眼睛对视了。他似乎明白了什么,脸上闪过一丝笑意。从布包里摸出两只茨菇,折下柄,一人一根,分给我俩。小手很瀴,茨菇柄也没什么热的感觉。我们塞进嘴里,一嚼一咽,就没了。
其实,茨菇有点苦味。只是在没零食的童年里,看父亲茨菇过酒,太有味道了。那场景,刻骨铭心。许多年后,我从同事结婚时的半碗黄酒起,夏季的啤酒,冬天的黄酒,还有红酒,白酒,喝成了一个老酒徒。这下酒的菜中,冬季的茨菇,成了我雷打不动的“伴”。
茨菇,入菜喜欢轧荤堆。儿时,家里过年才杀鸡。除了白斩鸡,鸡头、鸡翅、鸡脚,与茨菇炒了,它便是我家年夜饭的一道传统小菜。还有,难得的红烧肉,也请茨菇作伴,其目的之一是让这碗菜满一点。
如今,尽管菜场里的各种荤素菜,应有尽有。但一旦茨菇上市,我家在整个冬天就有它一席之地。就是吃法单一了,每餐蒸熟几只,下酒时,与坚果一起作一种闲菜,让它一次次引我回望父亲那茨菇过酒的冬天。
几十年来,养成的扳茨菇柄,撕茨菇皮,“脱”皮上的肉,这一串吃茨菇的动作,我知道,俨然父亲的翻版。如果我的儿孙们见了,特别是“脱”皮的腔调,心想,他们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。
喔,真正不可思议的是,那个冬日,父亲为出行御寒,用茨菇过酒,五味杂陈。乡间有俗语:“一尺布遮哈身,一开酒暖烘烘。”它戏谑的是,穷困人穿不上好棉衣,无奈以小酒驱寒的艰辛。就在这一天,父亲放下酒碗后,母亲在他旧棉袄间缚了一条布腰带,肩膀上披了幅旧布,“整装待发”的父亲,因为家里没有手电筒,便提了盏祖上留下的纸灯笼,在亲妈(祖母)和母亲一遍遍“当心,当心”的叮嘱中,出门走进风雪里,沿汉塘纤堤,到小镇偏远的南乡九曲村,去完成一次送信的差使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,乡村没电话,政府的通知、信件,随时由“管制”人员步行送达。我父亲,时在管制中。
第二天,母亲告诉我,父亲半夜回家时,棉裤湿了半条,她连夜用脚炉烘干……
呵!茨菇的冬天,曾为陪伴我父亲风雪夜的奔波,独自奉献了一餐至今未散席的美宴。只是现在茨菇的口感少了苦味,就连数九寒天,也再没像儿时那么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