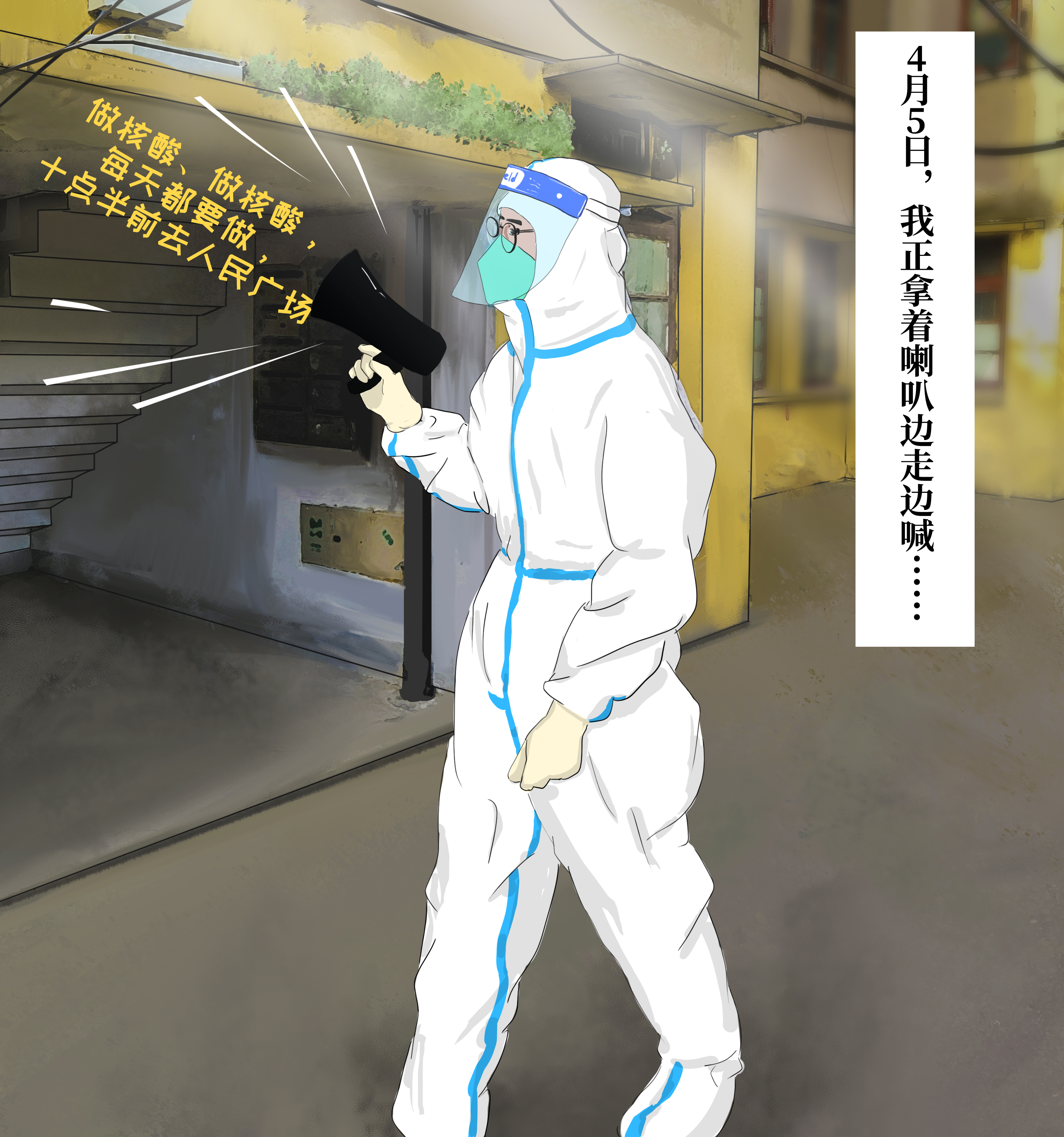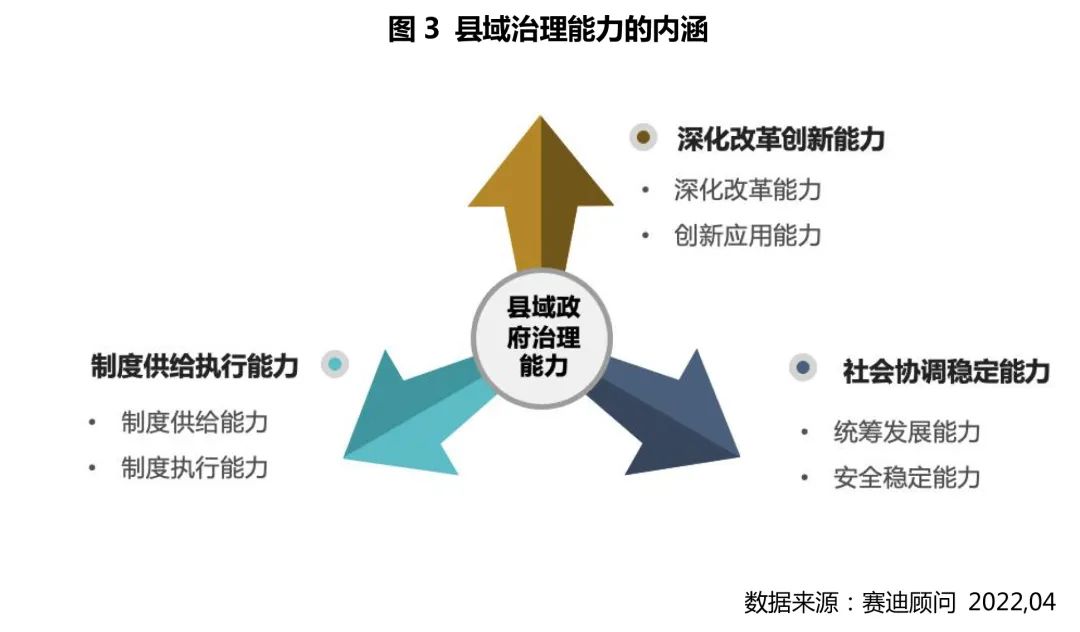校门口 供图 陈渊
人到中年以后,经常会不经意想起某个人或者某个场景,而这些回忆,大概就七拼八凑填满了人生。
G君是我偶尔会想起的一个少年朋友,几年不通音讯,微信忽然问候一声,没有任何阻碍,各自汇报近况。“大娃考进西安交大少年班”“15岁”G 说。15岁,正是我认识G君的年龄。
我是在卫校广播室的阁楼上第一次见到G君的,那年我才中专一年级,负责一档音乐节目的编辑,懵懵懂懂又有些孤傲,G君比我高一年,却又比我小一岁,属于少年老成,他是播音员,笑起来总是腼腼腆腆露出一口白牙。节目很受欢迎,同学们的来信经常塞满班级的信箱。我时常在课余的时候,听着G君念着我的文字,一个人漫步校园,低缓的叙述和缠绵的港乐萦绕校园四季的花园和朦胧的晨昏,在枯燥的医学知识里,有了一丝斑斓。或许我对文字和音乐的偏爱也是在那些时候得以加深和镂刻的。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还一起策划主持了一次全校的音乐比赛,邀请了嘉兴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的负责人,一时盛况空前。
后来,渐渐发现,G是个全才,学校运动会上他几乎满场飞,我在赛道上跑新闻,见他在长跑的队伍里一骑绝尘,学校门口的黑板报也常见他在琢磨,他的板书和硬笔书法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好的,我没有问过他会不会画画,但那惟妙惟肖的插图,我也总觉得与他有关。
这些字,等到他先我一年毕业后,时常以书信的形式出现在我的桌前。他就像一个成熟稳重的兄长,不忘督导我好好念书,用龙飞凤舞的书法字体,给我写人生格言: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可是在紧要处只有几小步,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那时,他在一个遥远闭塞的矿区医院,我不知道以他那多才多艺的性格,是怎么忍受最初的煎熬与空乏的。
等再相见时,是他调回杭州后,我也已经工作了几年。他没有什么变化,依然清瘦、挺拔,围棋、桥牌、篆刻是他业余时间的内容,时常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比赛。以后,时间慢慢流淌,我成了家,做了母亲,若去杭州培训,他一定会来看我,坐在酒店的大堂里聊天,会细心准备水果,带我去附近用餐。
他的第一次婚姻并不顺利,在我的孩子都能打酱油的时候,本就结婚晚的他又恢复了单身。那时,我并不懂如何安慰一个情感失意的人,而这个人长期以来是以一个长兄的身份在引导你,但事实上生理年龄又比你小。但我总觉得,聪明如他,总会拥有幸福,晚一些来而已。
现在,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,竟然已经把十五岁的大娃送进了大学少年班。我想起那些十五六岁时候的黄昏,我爬上木质楼梯,踩在咚咚作响的陈旧木质地板上,清瘦的少年坐在简陋的播音台前调试设备。有时,我们也会为了坚持各自的观点而有分歧,相持不下的时候,少年用好看的硬笔书法字体在废弃的报纸上写一句抱歉的话。有时,我会站在广播室的窗前,透过狭小的瞭望窗口,向空荡荡的大礼堂望去,空无一人的舞台上,似乎还有记忆中那一道耀眼的追光和呼啸的掌声。那是青春啊!
我记得问过G,为什么会早两年读书?记忆中G抓抓浓密的头发,憨厚地笑:“小时候没人管,又太皮了,所以就去读书。”
编辑:周伟达
责编:邓钰路